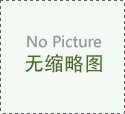七佛译师两次“破戒”娶妻,因正史记载而扑朔迷离,今或可澄清
发布时间:2023-10-16 01:24:51作者:金刚经福音网我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,为佛教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其伟业永载史册,受到世人长久敬仰。然而,鸠摩罗什译经传法过程中发生的“破戒”事件,使其受到了各种议论。鸠摩罗什的“破戒”,宛如美玉中的一点瑕疵,让人感到莫大的遗憾和困惑。对鸠摩罗什的“破戒”问题,古今中外人们早有评说。佛教界、历史学界、文学界从不同的角度都有分析、论说甚至渲染。从学术研究角度看,关于鸠摩罗什“破戒”的问题,还需要在史料上下更大功夫,使之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。
我们先解题。
七佛译师
“过去七佛译经师,颖悟绝伦善知识。恩播法界泽后世,大教流通永护持。”
七佛译师的典故,出自《道宣律师感通录》:
唐朝的时候,终南山有位道宣律师,专门修持戒律,由于持戒精严,感应了天人给他送饭。有一天,道宣律师因为年老,走路不小心跌倒,北方多闻天王的儿子就来把他扶住了。他一看是天人来护持,就问:为什么世间人都欢喜读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呢?天人就对他说:鸠摩罗什法师是过去七佛的译经师──过去七佛所说的经典都由他来翻译──因为他生生世世都发愿:“有佛出世,我就要来翻译经典!”从过去七佛到现在,都是他翻译经典;也因为这样,所以他翻译的经典,非常可靠。
以下正式讨论鸠摩罗什“破戒”问题。
三篇记载
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,最主要的三篇:
(1)南朝梁僧祐撰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四《鸠摩罗什传》;
(2)南朝梁慧皎撰《高僧传》卷二《晋长安鸠摩罗什》;
(3)《晋书》卷九十五《艺术传·鸠摩罗什》。
以上材料,《出三藏记集》与《高僧传》内容基本相同,少部分有差异;《晋书》内容是以上两篇的摘录和缩编,但有很大的增删。
关于鸠摩罗什“破戒”的记载,《出三藏记集》与《高僧传》是相同的,只是词字略有差别。
按上述两篇所记,与鸠摩罗什“破戒”相关的两次事件,以下引《高僧传》所载。
两次“破戒”
鸠摩罗什第一次“破戒”是在前秦建元二十年(384),苻坚派吕光破龟兹获鸠摩罗什后。
光军未至,什谓龟兹王白纯曰:国运衰矣,当有勍敌。日下人从东方来,宜恭承之,勿抗其锋。纯不从而战,光遂破龟兹,杀纯,立纯弟震为主。光既获什,未测其智量,见年齿尚少,乃凡人戏之,强妻以龟兹王女,什拒而不受,辞甚苦到。光曰:“道士之操,不逾先父,何可固辞。”乃饮以醇酒,同闭密室。什被逼既至,遂亏其节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,欲使堕落。什常怀忍辱,曾无异色,光惭愧而止。
第二次是前秦灭亡后,后秦君主姚兴迎罗什入长安,拜为国师。罗什主持庞大译场,译出大量佛经,取得极大成就和声望。姚兴视罗什为奇才“圣种”,唯恐断后,便强迫罗什接受女人,以“传种接代”。
什为人神情朗澈,傲岸出群,应机领会,鲜有论匹者。笃性仁厚,泛爱为心,虚己善诱,终日无倦。姚主常谓什曰:大师聪明超悟,天下莫二,若一旦后世,何可使法种无嗣?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。自尔以来,不住僧坊,别立廨舍,供给丰盈。每至讲说,常先自说譬喻:如臭泥中生莲花,但采莲花,勿取臭泥也。
从这两处记载看,鸠摩罗什“破戒”的情况是清楚的。第一次是“什被逼既至,随亏其节”,第二次是“逼令受之”。尽管有学者批评鸠摩罗什“定力不足”“不如柳下惠”,但两次均非出于自愿,完全是被迫的。
被迫还是主动?
可是《晋书》的一段文字,却改变了前面记载的“被迫”性质。《晋书·鸠摩罗什传》有下面一段:
尝讲经于草堂寺,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,肃容观听。罗什忽下高座,谓兴曰:有二小儿登吾肩,欲鄣须妇人。兴乃召官女进之。一交而生二子焉。
正是这段文字,使鸠摩罗什“破戒”的问题,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,同时对鸠摩罗什的人品、行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对这条文字记载,历来就有争议,主要态度有3种:
(1)否定;
(2)怀疑;
(3)赞同。
《晋书》的记载可靠吗?
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,确定《晋书》记载的可靠性如何。
笔者是史学专业出身。专业训练教给我们看待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、历史现象的原则是“未经批判的不轻信”,总的方法是“实事求是”。为此,就要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材料”,穷尽一切可能的材料,一手二手三手的都应收集;还要全面分析材料,分析前人如何看待这些材料,防止断章取义;更要分析材料的来源、材料组织者的意图,即文本背后的密码。
相对来说,记录越靠前,可靠性越高。在这点上,《出三藏记集》《高僧传》无疑是胜过《晋书》的。
人们历来对《晋书》有不同的评价,除肯定其历史价值外,不乏对其史料不确等方面提出严厉的批评。对于《晋书》的那段记载,许多学者都曾表示怀疑。
(1)“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”
目前流传于世的《晋书》,是唐初由唐太宗李世民下“修晋书诏”要求重修的,以南朝齐臧容绪撰《晋书》为底本,兼引十六国史籍,经2年撰成。唐修《晋书》比较全面广博,史料丰富完整,“参考诸家,甚为详洽”。但《晋书》也存在不少问题,主要是以野史逸闻如《世说新语》《幽明录》《搜神记》中的神怪传说作为史料收人书中。
《晋书》完成不久,就受到指责,《晋书》监修者房玄龄说该书“史官多是文诵之士,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,又所评论,竟为绮艳,不求笃实。由是多为学者所讥”。可见问题不小。
唐代著名史学家徐坚对这部《晋书》非常不满,自己另私修《晋书》与官修《晋书》分庭。
唐代另一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其《史通》中屡次批评《晋书》中的错讹失实的问题,称《晋书》“好采小说,论赞不实”“务多为美,聚博为功,虽取说于小人,终见嗤于君子矣”。此后批评《晋书》者不绝于史。
清代“乾嘉学派”,对《晋书》考证研究更为深入。张熷在《读史举正》中揭出《晋书》谬误450余条。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批评《晋书》:“好引杂说,固多芜秽

现代学人也指出《晋书》采用了大量道听途说未经证实的材料,而贸然写入正史。吕思勉先生说:“《晋书》好博采而辞缺断制,往往数行之间,自相矛盾,要在知其体例,分别观之耳。”
上述《晋书》鸠摩罗什那段文字,就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。我们目前尚无法考证出其资料的准确来源,但《晋书》这段文字和后面鸠摩罗什“吞针”的故事,充满诡异色彩,与收入的其他荒幻故事一样,可能是从某些“小说”中摘取的,是“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”的事例之一。根据以上的情况,许多中外史学家在评说鸠摩罗什生平时,都认真考虑《晋书》这段文字的可靠性,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。
(2)“往往数行之间,自相矛盾”
《晋书·鸠摩罗什传》可能是从《出三藏记集》和《高僧传》摘录合编的。《晋书》与《出三藏记集》《高僧传》二书所载鸠摩罗什传记,有许多矛盾之处。鸠摩罗什向姚兴“索要女人”和“一交而生二子”的一段文字,与前后文有生硬嵌入的感觉。这段文字加在“姚主常谓什曰:‘大师聪明超悟,天下莫二,若一旦后世,何可使法种无嗣。’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”之前,这就明显产生了前后矛盾。既然鸠摩罗什主动索要女人,姚兴即召宫女与罗什交配,并生了二子,为何后来召来的妓女十人还要“逼令受之”?这段文字岂不正是“往往数行之间,自相矛盾”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吗?《晋书·鸠摩罗什传》还有许多错讹之处,例如传记一开始说“鸠摩罗什,天竺人也,世为国相”。鸠摩罗什“世为国相”是明显的错误,按《高僧传》所记应是“家世国相”。这样的错误还不少。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,可见《晋书》作者编写的粗糙和不严谨。
(3)“兆见星象,驱役鬼神”
《晋书》将鸠摩罗什列入“艺术传”,其用意也是值得探究的。《晋书》“艺术传”共载24人。这些人的传记全都突出描述他们的占卜、图谶、秘纬、医术、星算、阴阳等能事。“艺术传”实际上就是“方术”类的传记。这24人中道教徒居多,佛教徒中在历史上有名望的只有鸠摩罗什和佛图澄。为了表示鸠摩罗什的“超自然”的能力,除了“一交而生二子”的“神异”能力外,紧接着加入了更为离奇的“吞针”故事:鸠摩罗什“索要女人”后,其他僧人要效法,于是鸠摩罗什用“吞针法术”制止了僧人的娶妻成家的奢望。
众僧多效之,什乃聚针盈钵。引诸僧谓之曰:能见效食此者,乃可畜室耳。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。诸僧愧服乃止。
这段文字也是始于《晋书》。“一交而生二子”和“吞针”是最符合《晋书》“方术”所要求的神异故事。
同样,佛图澄的传记也突出此方面的描述,如一开始就渲染佛图澄腹有一洞,夜间读书时,洞中发光和斋日将肠取出在水中洗涤的“神异”故事(《高僧传》将此事放在传的最后)。所以,《晋书》为鸠摩罗什、佛图澄立传是有其预定的设想,《晋书》作者的这种观点和态度在“艺术传”最后的结语中,表达得十分清楚:
澄、什爰自遐裔,来游诸夏。什既兆见星象,澄乃驱役鬼神,并通幽洞冥,垂文阐教,谅见珍于道艺,非取贵于他山,姚(兴)、石(勒)奉之若神,良有以也。
在这里《晋书》作者虽然也有所赞词,但鸠摩罗什只不过是位“兆见星象”的术士,佛图澄也只是“驱役鬼神”的巫师。
《晋书》立“艺术传”是因效仿前代艺术史记,但从总体看,《晋书》对此类事迹是轻贬的:“详观众术,仰惟小道,弃之如或可惜,存之又恐不经。”
“艺术传”最后的结语是:“硕学通人,未宜枉辔”,“传叙灾祥,书称龟筮,应如影响,叶若符契,怪力乱神,诡时惑世,崇尚弗已,必致流弊。”
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,对鸠摩罗什等人的事迹,自然就会缺乏全面而严肃的择汇史料,也不会准确公允阐述其历史功绩。
鸠摩罗什的译经是其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,但《晋书》只轻描淡写地说“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”,整篇传记突出的就是鸠摩罗什的经历和“趣闻轶事”。同《出三藏记集》《梁高僧传》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鸠摩罗什传记相比,《晋书·鸠摩罗什传》的记述与评价有明显失准、失衡的方面。故《晋书》所述鸠摩罗什的两件事迹,矛盾显见,颇为可疑。
两晋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,佛教译经也进入繁荣时代,出现了一大批佛教高僧,著名的有竺法护、帛尸梨蜜多罗、佛陀耶舍、县摩流支、朱士行、法显、释道安、慧远、鸠摩罗什、昙无谶、佛图澄、支遁等。这些高僧不仅在传播佛教上颇有建树,也为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《晋书》除了“艺术传”收了鸠摩罗什和佛图澄外,均无这些人的传记,后人对此多有微词,如陈垣先生对《晋书》不载“最负高名”的东晋支道林(即支遁)事迹不以为然。这种对佛教采取抑制的态度,应当与唐太宗“先道后佛”的偏执政策有直接的关系。
除了《晋书》那一段文字外,其他史籍上对鸠摩罗什“破戒”,大多用《出三藏记集》《高僧传》的记载,认同被迫的说法。
总结
《晋书》记载的不可靠性已如上述。绝大多数严肃的学者,对于《晋书》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是偏向于否定的。佛教界一些大德未深究史料,作出对鸠摩罗什显示神通“吞针”的解读,其实另有深意。三界唯心,万法唯识,关键在于用心、护心。神通确实是存在的,但它只是修行的副产品,不必执着。
下一篇,我们将讨论鸠摩罗什对自己“破戒”所持的态度,以及佛教界对其显示神通“吞针”的解读的深意。这样,我们对于鸠摩罗什“破戒”的问题会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深刻的认识,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法身慧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