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萨仁波切:个人快乐的定义
发布时间:2024-11-30 01:20:04作者:金刚经福音网
宗萨仁波切:个人快乐的定义
我们许多人从所处的社会学会快乐和痛苦的定义,社会秩序规定我们衡量满足的标准。这是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。来自世界两端的人,能够基于完全相反的快乐文化指标,却体验完全相同的情感——愉悦、厌恶或恐惧等。鸡爪是中国人的佳肴,法国人则喜爱把吐司涂在肥鸭肝上。如果资本主义从不曾存于世界上,而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确切实践毛泽东务实的共产哲学的话,想象一下世界会变得如何:我们会很快乐地活在没有购物中心,没有豪华的汽车,没有星巴克,没有竞争,没有贫富差距,享有全民保健的社会。而脚踏车会比悍马休旅车更有价值。然而,我们的欲求是学习而获得的。十年前,在偏远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,卡式录放影机是富裕的象征。逐渐地,丰田Landcruiser越野车俱乐部取代了录放机俱乐部,成为不丹繁荣快乐的终极愿景。
这种把群体标准视为个人标准的习惯,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。小学一年级时,你看到其他同学都有某种铅笔盒。你发展出一个“需求”,要有和其他人一样的铅笔盒。你告诉了母亲,而她是否为你买那个铅笔盒,就决定了你的快乐水平。这个习惯持续到成年。隔壁邻居有一台电视或一辆崭新的豪华休旅车,因此你也要拥有同样的——而且要更大、更新的。渴望并竞相拥有他人所有的事物,也存在于文化层面中。我们常常对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传统,比自己的评价还高。最近,台湾有位教师决定蓄起长发,这在中国是个古老的习俗。他看起来高贵优雅,仿如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,但是校长却威胁他,如果他不遵从“规矩”——意即西式的短发,就要把他开除。现在他把头发剪得短短的,看起来好像被电击了一样。
目睹中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难为情,令人讶异。但是在亚洲,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诸如此类的优越或自卑的情绪。一方面,亚洲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,但在另一方面,又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点令人反感或落后。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层面,他们都用西方文化来替代——举止、衣着、音乐、道德规范,甚至西方的政治体系,都是如此。
在个人和文化两方面,我们采取外来的和外在的方法,来获得快乐、克服痛苦,却不了解这些方法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。我们的不适应带来了新的痛苦。因为我们不仅仍在受苦,而且更觉得从自己的生活中疏离,无法融入体制之中。
有些快乐的文化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。一般来说,银行帐号里有一点钱、舒适的住所、足够的食物、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条件,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快乐。但是,印度的苦行僧和西藏走方的隐士之所以感到快乐,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锁匙圈——他们不必恐惧财产会被人偷走,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锁起来。
问一个佛教徒“什么是人生的目的?”是不恰当的。因为这个问题暗喻在某一个地方,也许在一个洞穴之中或者在一个山岭之上,存在着一个究竟的目的。仿佛我们可以透过追随圣者,阅读书籍以及熟悉密教修行,来解开这个秘密。如果这问题是假设在亿万年以前,有某个人或神设计了一个人生目的图表,那么这就是一个有神论的观点。佛教徒不相信有个全能的创造者,而且他们不信生命的目的已经、或需被决定和定义。
对佛教徒比较适当的问题是“什么是生命?”。从我们对无常的了解,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非常明显: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和合现象,因此生命是无常的。它是随时变化、短暂、无常经历的集合。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生命形式存在,但其共通点是没有一个生命希望受苦。我们都想要快乐,无论是总统、亿万富豪,或辛勤工作的蚂蚁、蜜蜂、虾子和蝴蝶,大家都想要快乐。
当然,在这些生命形态中,痛苦和快乐的定义有极大的区别,即使在范围相对较小的人道之中,也是如此。对某些人痛苦的定义,是其他人快乐的定义,反之亦然。对某些人而言,只要能生存下去便是快乐,对另外的人而言,拥有700只鞋子是快乐。有些人,在臂膀上有个贝克汉姆模样的刺青就会快乐。当一个人的快乐取决于享有一片鱼翅、一根鸡腿或一根虎鞭时,快乐的代价是另一个生命。有些人觉得用羽毛轻搔是性感的,另一些人则偏爱乳酪碎磨器、皮鞭和链圈。英国爱德华八世宁愿娶一个离过婚的美国女子,也不要戴上大英帝国的王冠。
即使在个人身上,痛苦和快乐的定义也时有变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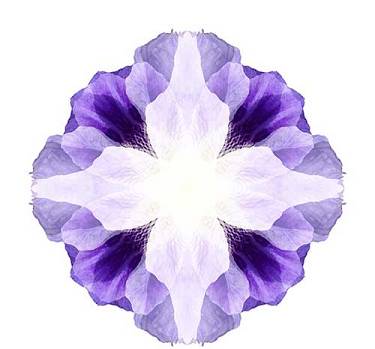
我们许多人从所处的社会学会快乐和痛苦的定义,社会秩序规定我们衡量满足的标准。这是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。来自世界两端的人,能够基于完全相反的快乐文化指标,却体验完全相同的情感——愉悦、厌恶或恐惧等。鸡爪是中国人的佳肴,法国人则喜爱把吐司涂在肥鸭肝上。如果资本主义从不曾存于世界上,而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确切实践毛泽东务实的共产哲学的话,想象一下世界会变得如何:我们会很快乐地活在没有购物中心,没有豪华的汽车,没有星巴克,没有竞争,没有贫富差距,享有全民保健的社会。而脚踏车会比悍马休旅车更有价值。然而,我们的欲求是学习而获得的。十年前,在偏远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,卡式录放影机是富裕的象征。逐渐地,丰田Landcruiser越野车俱乐部取代了录放机俱乐部,成为不丹繁荣快乐的终极愿景。
这种把群体标准视为个人标准的习惯,在幼年时就开始形成。小学一年级时,你看到其他同学都有某种铅笔盒。你发展出一个“需求”,要有和其他人一样的铅笔盒。你告诉了母亲,而她是否为你买那个铅笔盒,就决定了你的快乐水平。这个习惯持续到成年。隔壁邻居有一台电视或一辆崭新的豪华休旅车,因此你也要拥有同样的——而且要更大、更新的。渴望并竞相拥有他人所有的事物,也存在于文化层面中。我们常常对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传统,比自己的评价还高。最近,台湾有位教师决定蓄起长发,这在中国是个古老的习俗。他看起来高贵优雅,仿如一个古代的中国战士,但是校长却威胁他,如果他不遵从“规矩”——意即西式的短发,就要把他开除。现在他把头发剪得短短的,看起来好像被电击了一样。
目睹中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难为情,令人讶异。但是在亚洲,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诸如此类的优越或自卑的情绪。一方面,亚洲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,但在另一方面,又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点令人反感或落后。几乎在所有的生活层面,他们都用西方文化来替代——举止、衣着、音乐、道德规范,甚至西方的政治体系,都是如此。
在个人和文化两方面,我们采取外来的和外在的方法,来获得快乐、克服痛苦,却不了解这些方法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。我们的不适应带来了新的痛苦。因为我们不仅仍在受苦,而且更觉得从自己的生活中疏离,无法融入体制之中。
有些快乐的文化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。一般来说,银行帐号里有一点钱、舒适的住所、足够的食物、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条件,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快乐。但是,印度的苦行僧和西藏走方的隐士之所以感到快乐,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锁匙圈——他们不必恐惧财产会被人偷走,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锁起来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