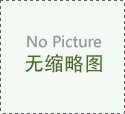啊,莲花
发布时间:2024-08-19 01:23:47作者:金刚经福音网啊,莲花 涯舟闽南佛学
今年暑假,我从杭州回到南普陀寺。一走进山门,宽阔的莲花池里那一片郁郁的碧色,就委实让我吃了一惊。记得去年离寺赴杭求学时,这里还不过是一个长满水草的荒池呢i随即又兴奋不已,想不到在杭州留下的遗憾,竟在这里得到了补偿。 我是去年九月上旬到杭州的,在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深造。学院就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。课余,便登上丹桂飘香的玉皇顶;冒寒踏雪保俶塔下断桥边;徜徉在“杨花沾人衣”的苏堤。一旦触动诗的灵感,也吟上一二首,让自己陶醉在旖旎的湖光山色之中。挥挥手,两个学期便过去了,总以没机会领略那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十里胜景为憾事;当时,只匆匆地瞥上一眼那刚伸出水面嫩绿的莲叶,便登上南下的列车。 这一池浓浓的碧莲,突然展现在眼前,怎能不令人又惊又喜呢? 厦门的夏天来得早,莲叶已经长得很肥很盛了。亭亭玉立的莲干撑着圆圆的翠绿色的盖,托着晶莹的小露珠,在晨风中微微地摇曳着,伸展着;莲花这时候还浸在水下的污泥里,没能长出水面。我只能想象“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”的清丽景色了。 此后,莲花池便是我经常徜徉的地方,即便是烈日炎炎的中午,也不忘绕池走上一遭。浓浓莲荫下,青蛙懒懒地蹲着;挺着肚子,偶而叫上一两声,也是有气无力的。粉红色的莲花夹杂着尖尖的莲箭子,轻轻地伸出水面;一群游鱼在莲花、莲叶中间,似乎跟我一样毫无倦意地穿来穿去。我不禁想起乐府的诗意。现在,虽然还不是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睑两边开”的江南采莲女划着小舟采莲的时节,但是,若有雅兴漾着轻舟,藏入莲叶深处,也不妨以茶代酒,赏花、赋诗,也当另有一番风趣。 莲花与佛教是很有渊源的。天竺(印度)有青、黄、赤、白四种颜色的莲花,梵文分别称作优钵罗、拘物头、波头摩、芬陀利花。尽管颜色品种要比中土的莲花丰富,但想来并不见得比中土的莲花大多少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,就不是寻常的。《阿弥陀经》云:“池中莲花大如车轮,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,微妙香洁。”不但花大薰人,而且还散着种种不可思议的光呢!这不能说不神妙了。莲花生长于污泥,娉婷于水面,开放于炎热的夏季。在佛教里,把炎热比喻为烦恼,把水比喻为清凉,把花比喻为清净。意思是愿人们发心超离这烦恼秽浊的娑婆世界,即通过自己种种善的行为,使心中的烦恼得以消除,进而达到圣洁、喜乐、光明(心灵的净化,精神的升华)的境界——净土世界。 以庄严国土、净化人生为宗旨的佛教,用圣洁的莲花作为象征,这再合适不过了。 在中国,东晋高僧慧远住锡庐山,与刘遗民等人同修净土,即把社团,命为“白莲社”,开风气之先。隋唐以降,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,它的象征物——莲花,也自然更直接、更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。无论文学、雕塑、陶瓷、绘画、建筑,都可见到她的存在与价值。寺庙里更是随处可见,柱子、粉墙、旗幡、炉鼎…… 有一次,我从大悲殿前面经过,这是一个铺满刻着莲花浮雕的花岗石地砖的平台。无意间,发现她们身上满是狼籍的脚印;柔美的线条,早被磨成为浑重的轮廓;昔日的光彩,早已不复存在,只剩下一身无奈的憔悴和创伤。但并不因此而止,人们依然不断从她们身上踩过踏过